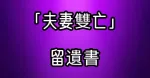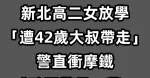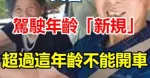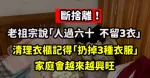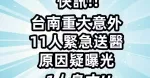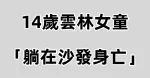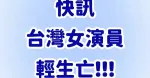3/4
下一頁
妻子19歲早逝,他跪在棺木前3天3夜,之後對岳父發誓:終身不再娶

3/4
彼時,馬一浮正在一間印刷鋪里與同伴爭論版式,收到急電後他整個人呆立當場,手像被抽走了骨架的紙人。
他不顧一切,連夜乘船南下,車馬奔波,途中幾次差點暈厥。
推開湯府的大門時,迎接他的不是妻子嬌羞的笑臉,而是棺木中安詳如眠的湯儀。
他撲在棺木前,泣不成聲,過去的點點滴滴一幕幕閃回。
他跪了三天三夜,不言不語,不食不飲,有人試圖勸解,他無動於衷;有人送上熱湯,他只是緩緩搖頭。
湯壽潛也出現在他身後,滿臉疲憊。
老人雖已白髮蒼蒼,仍強撐著悲痛安慰:「福田,人死不能復生,你日子還長。」
馬一浮淚眼模糊,卻又神情堅定:「岳父在上,今日起,我馬一浮此生不再娶,人世間,黃泉下,唯有湯儀一人是我妻,若違此言,天打雷劈,死後下十八層地獄。」
湯壽潛頓時怔住,眼中閃過複雜情緒:有憤恨,有不舍,也有隱忍的感動。
自此之後,馬一浮謝絕一切親事,再無兒女情長,他將自己的溫柔、悔意、眷戀,統統埋在那一口棺中,從此以學問為伴,與孤獨作友。
他不再提湯儀,卻在每年梅花初開之時,前往她墓前,焚香一爐,灑酒三杯。
守寡一世
妻子去世後的第二年,馬一浮便只身前往美洲,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海外遊學生涯。
他投身德國、西班牙,繼而東渡日本,鑽研西方哲學與語言,夜以繼日。
那些年,他攻讀《資本論》,深入研究康德、黑格爾、叔本華,甚至帶著書稿與思想往返歐亞大陸,只為將西學精髓引入中國。
在那些深夜,別人只看見一個伏案而寫的學者,卻不知他每次閉眼歇息時,夢中總會浮現那個清瘦的身影。
他不是不懂情,而是把最深的那份情,壓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,封存六十年,不再提及。
馬一浮回國後,便成了新思想的旗手,他支持辛亥革命,親撰宣言,鼓吹民主;又投身教育改革,培養後學。
他學識淵博、談吐儒雅,廣受讚譽。
蔡元培、梁啟超、章太炎都與他往來密切,敬之如師。
但他們中沒人知道,他每次赴宴或演講之前,都會在書桌角落那幀湯儀舊照前停留。
人們勸他再娶,他婉拒,蔡元培一度想為他引薦名門閨秀,馬一浮卻搖頭拒絕。
岳父湯壽潛也曾試圖勸他改嫁,甚至以自家三女相許,希望他能有後繼,馬一浮依舊拒絕了。
時間是最鋒利的刃,但馬一浮的誓言,卻在風雨中愈顯堅定。
他自三十歲後,從未再置婚事,不收妾、不納侍,不近女色,獨居書齋,與經史為伴。
歲月流轉,政權更替,新中國成立後,他應邀赴京,受到毛主席親見。
主席與他暢談古詩詞,他作對相贈,周總理、陳毅等人亦對他敬重非常,常邀他赴宴,聆其講學。
但他從不借勢,只潛心治學。
他不顧一切,連夜乘船南下,車馬奔波,途中幾次差點暈厥。
推開湯府的大門時,迎接他的不是妻子嬌羞的笑臉,而是棺木中安詳如眠的湯儀。
他撲在棺木前,泣不成聲,過去的點點滴滴一幕幕閃回。
他跪了三天三夜,不言不語,不食不飲,有人試圖勸解,他無動於衷;有人送上熱湯,他只是緩緩搖頭。
湯壽潛也出現在他身後,滿臉疲憊。
老人雖已白髮蒼蒼,仍強撐著悲痛安慰:「福田,人死不能復生,你日子還長。」
馬一浮淚眼模糊,卻又神情堅定:「岳父在上,今日起,我馬一浮此生不再娶,人世間,黃泉下,唯有湯儀一人是我妻,若違此言,天打雷劈,死後下十八層地獄。」
湯壽潛頓時怔住,眼中閃過複雜情緒:有憤恨,有不舍,也有隱忍的感動。
自此之後,馬一浮謝絕一切親事,再無兒女情長,他將自己的溫柔、悔意、眷戀,統統埋在那一口棺中,從此以學問為伴,與孤獨作友。
他不再提湯儀,卻在每年梅花初開之時,前往她墓前,焚香一爐,灑酒三杯。
守寡一世
妻子去世後的第二年,馬一浮便只身前往美洲,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海外遊學生涯。
他投身德國、西班牙,繼而東渡日本,鑽研西方哲學與語言,夜以繼日。
那些年,他攻讀《資本論》,深入研究康德、黑格爾、叔本華,甚至帶著書稿與思想往返歐亞大陸,只為將西學精髓引入中國。
在那些深夜,別人只看見一個伏案而寫的學者,卻不知他每次閉眼歇息時,夢中總會浮現那個清瘦的身影。
他不是不懂情,而是把最深的那份情,壓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,封存六十年,不再提及。
馬一浮回國後,便成了新思想的旗手,他支持辛亥革命,親撰宣言,鼓吹民主;又投身教育改革,培養後學。
他學識淵博、談吐儒雅,廣受讚譽。
蔡元培、梁啟超、章太炎都與他往來密切,敬之如師。
但他們中沒人知道,他每次赴宴或演講之前,都會在書桌角落那幀湯儀舊照前停留。
人們勸他再娶,他婉拒,蔡元培一度想為他引薦名門閨秀,馬一浮卻搖頭拒絕。
岳父湯壽潛也曾試圖勸他改嫁,甚至以自家三女相許,希望他能有後繼,馬一浮依舊拒絕了。
時間是最鋒利的刃,但馬一浮的誓言,卻在風雨中愈顯堅定。
他自三十歲後,從未再置婚事,不收妾、不納侍,不近女色,獨居書齋,與經史為伴。
歲月流轉,政權更替,新中國成立後,他應邀赴京,受到毛主席親見。
主席與他暢談古詩詞,他作對相贈,周總理、陳毅等人亦對他敬重非常,常邀他赴宴,聆其講學。
但他從不借勢,只潛心治學。
 呂純弘 • 4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7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7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4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10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